海峽報導,在新加坡芽籠一個潮濕的星期二早晨,58歲的塞琳(Serene,化名)照例揹著帆布袋,走進一條條狹窄的巷弄。在第16巷附近,她看到兩名女子站在店屋外。
她用中文開口說:「我以前沒看過你們,你們是剛到嗎?」
其中一人露出有點戒備的微笑:「上個星期。」
她們聊起家鄉和食物,回答一開始都很簡短,直到塞琳問她們打算待多久,「就幾個星期,」那名女子說完,補了一句:「我不會逾期停留。妳是警察嗎?」
塞琳笑著否認:「不是啦,我只是在這一帶工作。」她說著,把一小包芭樂辣片塞進對方手裡。
塞琳任職於基督教團體,已經在當地紅燈區關懷超過10 年,她把自己的角色看作單純「表達關心」,「我們不是來『拯救誰』的」,「但如果看起來有人很煩惱,我們就會問,能不能幫上什麼忙。」
她每週看到的畫面——短短的對話、帶警戒的微笑、來來去去的女人——其實都連向一段更久遠的歷史:要理解她今天做的工作,就得回頭看,新加坡性交易是如何從殖民地時期一路發展下來的。
根據新加坡國立大學蘇瑞福公共衛生學院研究,新加坡約有 8,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。
1826年人口普查顯示,新加坡當時只有 13,750 名居民,卻已呈現嚴重性別失衡:華人男性 5,747 人,華人女性只有 341 人;印度男性 2,208 人,女性只有 40 人;馬來男性 2,501 人、女性 2,289 人。
這份普查凸顯了當時新加坡作為快速成長、男性佔壓倒多數的港口城市,對性工作者有多大的需求。
到了 1884 年,新加坡已有約 6萬名華人男性,卻只有 6,600 名華人女性,其中約 2,000 名廣東和潮州女子在妓院工作。
有學者推算,19 世紀末抵達新加坡的年輕華人女孩中,多達 80% 最後被賣進妓院。
有些女性是自己選擇進入性交易,但更多人是被貧窮推著走,或直接被家人賣掉。來自中國和日本鄉村的年輕女性,先途經長崎、廣州等港口,再被送往新加坡的妓院。
到 1905 年,中路(Middle Road)甚至被稱為「小日本」。官方紀錄顯示,當地密集分布著 109 間妓院,裡頭共有 633 名日本女子工作。
在性交易快速擴張下,殖民政府最後放棄「全面禁止」的做法,轉向「管制模式」,發牌管理妓院、規定醫療檢查,並透過 1870 年頒布的《傳染疾病條例》=訂下營業規則。
這種「不完全禁止、改以規範」的殖民治理思維,也延續到今天,形塑出新加坡既承認又限制性產業的複雜法律框架。
根據前述 2023 年研究,在約 8,030 名女性性工作者當中,大約 800 至 1,000 人在芽籠主要紅燈區內、超過 100 間受管制的妓院工作。這組數字並非官方統計,而是由前性工作者、以及每週到現場的志工外展員,以經驗推估出的範圍。

不過,這些「有牌照的妓院」只是整體樣貌中的一小部分。更龐大的地下經濟遠遠超出芽籠巷弄,延伸到按摩店、KTV、沙龍、應召仲介,甚至包括私密聊天頻道和 OnlyFans 等訂閱制平台,構成一整個線上線下交錯的市場。
即便如此,數字依舊非常「不穩定」。研究只估算了女性性工作者,並未把男性與跨性別工作者、在旅館或公寓單打獨鬥的「自由職業者」、規模很小的自組團隊、或被仲介「抽成」管理的工作者納入,所以真正的產業規模,很難被完全看清。
研究指出,多數性工作者是短期移工,以觀光簽證入境、停留幾星期就離開;新加坡公民與本地居民只佔很小一部分。本地人(包括永久居民和長期探訪簽證持有人)大約只佔整體從業人口的 15% 至 20%。
非營利組織 Project X 執行董事賀(Vanessa Ho)說,要精準說出她們「為何進入這個行業」並不容易,因為光用「性工作者」三個字,其實也遮蔽了很多現實,「一位單親媽媽的故事,和一位跨性別性工作者的故事會完全不同;從印尼來的,又會跟從中國或越南來的有巨大差異。大家的故事複雜得多,也細膩得多。」
她認為,把這些人唯一地拼成「被害者」或「道德問題」,忽略了她們共同面對的結構性壓力:債務、照護負擔、薪資停滯、保護不足,以及一個殘酷的現實——「這份工作確實能賺到錢」。
在新加坡,受管制的妓院會被官方監測健康與安全,裡面的性工作者必須定期接受性病與愛滋病毒檢查,並實施「100% 必須使用保險套」的政策,雖然實務上嚴格執行到什麼程度,外界很難得知。
新加坡的性產業地圖也不止於芽籠,長年被稱為「小泰國」的黃金坊,在 2023 年 5 月拆除重建前,曾是泰國移工聚集的夜生活據點;印度與孟加拉移工則多出現在小印度區的德加路(Desker Road)一帶。
直到許多店家在 2023 年失去公眾娛樂執照之前,烏節大廈(Orchard Towers)也以酒吧、夜店與燈紅酒綠的形象聞名。
在這些社區背後,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非正式安排:在網路上自我宣傳的自由接客者;視情況提供「額外服務」的按摩師;在表演與親密工作之間游走的酒店小姐;以及門面看似普通、走進第二道門後就變成另一個世界的店鋪。這些不斷變動的聚點,拼出新加坡性產業的地理版圖,也緊扣著不同移民潮與市場需求。
至於紅燈區對社區影響,有男性居民抱怨自己在街上被站壁女郎主動搭訕、直接報價;也有女性居民被誤認為性工作者。居民同時擔心,KTV 營業到凌晨 3 點帶來的噪音與酒駕問題,已影響社區安全。
同一時間,性工作者的組成也在變化:有人是「推到簽證邊界」的觀光客;有人是拿特別長期准證、為了補貼不穩定收入而兼職;也有人像 40 歲印尼籍永久居民黛薇(Dewi),選擇這份工作,是看重它的彈性——既能顧小孩,又能在先生收入不足時分擔家計。
儘管「性交易」本身沒有被明文禁止,但它周邊的很多行為卻是違法的:招攬嫖客、在無效簽證下工作、皮條客行為、經營無牌照妓院等。這造就了一個很窄的縫隙——一小部分在「受管制」的框架下運作,其他人則隨時面臨取締。
販運的徵兆;一旦發現有表面上的犯罪事實,才會進一步展開調查。
當有交易糾紛發生,弱勢的往往還是性工作者,某一起案件是性工作者報案指控客人拒付約定款項,還施以暴力。最後,客人確實被起訴並判刑,但這名報案人卻被關了 10 小時、手機被沒收,還被要求留在新加坡 3 個月配合偵訊,在這段期間只能睡在非營利組織辦公室的沙發上。
面對這樣的代價,很多受害者最後選擇沈默。
當案件浮上檯面時,也往往揭露非法性工作者在皮條客與客人手中遭受的剝削。2019 年,一名堆高機司機周在 KTV 結識一名越南籍表演者,聲稱願付 200元新幣(約4,700元台幣)到家中發生性行為,卻在事後拿刀恐嚇並強暴對方,最後被判刑 14 年、鞭刑 24 下。
2021 年,新加坡籍仲介陳男因剝削多名泰國籍性工作者,被判刑 15 個月,他替她們安排住宿,收走護照,要求她們「做滿合約」才能拿回證件,並額外收取 1,200 元(約2.8萬元台幣)「贖回費」,藉此阻斷她們離開的可能。
黛薇同樣對臨檢保持高度警戒。她工作的按摩店 24 小時營業,但多數性工作者會在早上接近中午才上工,待到深夜,輪流排早班。有散客上門,但店裡更偏好熟客,價格在發生任何行為前就談好,「一定戴套」是鐵則。
即便她是永久居民,在無牌妓院工作仍是一項足以顛覆她人生的罪名。她對家人隱瞞工作細節,希望再做幾年就能抽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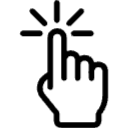 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點擊閱讀下一則新聞







